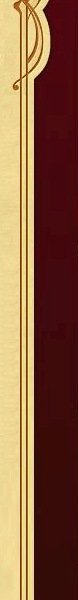第三章 大时代中流离
整个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,是近代中国最惨痛的年代。老百姓深深地陷入外侮侵凌及内战的苦难当中,整个中国大地,一如人间炼狱。这种乱世的灾情,东北地区比起中国的其他地方尤甚。
东北地区,早于二、三十年代已首当其冲地成为日寇侵华的基地,伪满政权的统治,军阀之间为权势和利益的挣峙,都造成民间极大的不幸。四十年代中期,经过中国人民的八年浴血抗战,日军宣布投降,东北伪满权崩溃,社会秩序迅即失控,坊间通货膨胀,兵贼难分的匪徒抢掠财物,一时间风声鹤唳,情况混乱不堪。
祸延佛学院
观音寺虽地处荒野,但亦难逃乱世的纷扰。1945年9月3日,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降,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,并没有令全寺上下几十个僧人欢心鼓舞。相反,由于附近地区日军撤离时的抢掠,寺中已空无资财、粮食。坊间物价的暴升,在老百姓自己生活都无以为继的情况下,外出化缘一整天也只能是无功而还。这种恶劣的境况经历逾月,事情并未因日军的完全撤离而息止,相反,贫苦的老百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了深山老林中的土匪。三天二日的从老林子里窜出到寺中来抢掠。真是福无重至,祸不单行,不多久,连俄国的军士,都因了解到此时中国东北处于无政府和真空状态下,猖狂谛越境抢劫。他们来势汹汹,横行无忌。
在圆照法师和专修老和尚还为观音寺的困境发愁之际,呼兰河发生了几十年来未遇的洪水泛滥之灾,附近多个县份都被洪水淹没了。临河而建的观音寺,竟一下子陷于泽国之中。眼看洪水不可能三天五日的就退去,专修老和尚站在高坡上,发呆地望着一望无际的水面,一字一句地对着学僧们说:
“东北已不宜久居,观音寺佛学院看来也无法办下去了,大家还是先回家再说吧!眼下东北也快要入寒冬了,再不走,恐怕也来不及了。”
老和尚没有流泪,脸上也没有悲情,然而这更令年青的学僧们难受。三年多来,住持和专修老和尚视学僧如子女,在他们的护荫下,才得以在雪国净土中修学法。现在天灾、人祸一并而来,何处再寻安身立命的净土?
1945年9月14日,日军宣布投降后的十一天,东北各地传开中共中央已决定东北成立东北局的消息,东北势必成为中共与国民党长期对峙抗争的根据地。这样一来,国共内战的局面,将在东北一触即发。
仓皇逃命,南下回乡
9月15日,来不及收拾被洪水浸湿过的衣物和经书等细软,来不及一一辞别寺中上上下下的法师和同学们,永惺,这位二十岁的年青僧人,仓惶地与难民一起,结伴南下,从此,展开了他坎坷的逃难之旅。
随着难民一起自哈尔滨南下,永惺起先是漫无目的的。心想,人生路不熟,四下都是扶老牵雏,推着木轮车,带着家当细软的逃难民众,连化缘的条件也没有,自己已是受戒的出家人,也只能往寺庙投去。于是一路就朝家乡的方向逃去,那里有自己剃度出家的增福寺,也可顺道回家见见父母的面。
永惺沿着铁路线南下,甫一上路,就遭一帮俄军蜂涌而至,随身的衣物被洗劫一空。从此,他孑然一身,袋无分文,只知随着大批的难民,不分昼夜地辗转奔逃。正于饥寒困顿,再无力前行之际,见到一列停在小镇站上的火车,人潮便如蜂蚁般爬上车厢。车厢塞满了,再也无法进入,人们就往车顶和两车厢的接榫处上拥。火车开动后,也由于实在人太多了,不断有人从车上往下掉,摔落在铁轨之上。这些不幸下坠的难民,有些被至身首异处,即时死亡。就是当时未立即死去者,但荒郊野外,身受重伤,定不获救。此外,更有死于车匪和盗贼手上。沿途鬼哭神嚎,血流飘杵,此际,永惺第一次正式地感受到,什么叫哀鸿遍野,什么叫人间地狱。在触目惊心的逃亡生涯里,他惊惶无助,身心俱疲,经十多天的奔波,终于神志不清,跌跌撞撞地倒在踏入增福寺的门槛上。
从浑浑噩噩中苏醒过来以后,永惺见到增福寺旧日的师友,想到一路上的可怕遭遇,眼泪簌簌地掉下来。常修老和尚安慰他说: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,看你现在瘦得不像话,先把身子养好再说吧!”
此时的永惺已虚弱的连做起来都有点困难,原来在路上他已病染伤寒,那是一种极致命的传染病。在寺中住下后,一直高烧不退,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。永惺的母亲,很快就接到儿子自哈尔滨脱难归来的消息,又知他途中经历诸多苦楚,一病倒卧床不起。她匆忙赶到寺中来,两母子多年不见,劫后重逢,恍如隔世。母亲衣不解带地照顾爱儿于病塌之上。
得到母亲不眠不休的细心照顾,十多天后,永惺慢慢地恢复过来。当勉强可以下床走动时,永惺对母亲说:“看来我这病也不是一时三刻就完全好过来,你照料我也不方便,况且我也该回去看看父亲和兄弟姊妹了。”
拖着未愈的病体,永惺随母亲回到家中暂住修养。经历过乱世的逃亡,大病不死,永惺倍感亲情可贵。他与众人欢聚家中,共享天伦。经过两三个月的调养,已差不多完全康复,并计划春节过后,就回增福寺去。
慈母离世、恩师非命
永惺在家中静静地调养病体的这几个月,是东北地区的政局翻天覆地的时期。这几个月来,国共两党的军队,都赶着进驻、争夺抗战胜利后日军退出的守地。政局不明朗,一切无人管治,老百姓生活无着,土匪流氓横行当道,打家劫舍,治安极差。永惺感到在哈尔滨所经历的时局又在眼前出现了,心里不由得有一阵阵的寒意。果然,不幸的事情竟真的降临。
就在十二月初八的晚上,家里突然来了一帮匪徒,打劫抢夺财物米粮不算,还毫无人性地往喝止匪徒抢掠的人举枪就打。可怜的老母亲残被枪伤,当晚就因无药治病而离世。
想到自己幼承慈训,出家前母亲一直爱护有加,最近几个月来更是悉心尽力的照拂,病中思量,深感恩亲的深重。母亲如今竟死于非命,永惺内心的悲痛之情可以想象。但死者已矣,感叹生逢乱世,投诉无门,只好逆来顺受地忍耐。
葬殓好母亲以后,永惺辞别父亲和兄弟姊妹,回凌源增福寺去了。他希望能回到寺中好好为乱世多难的众生、为自己不幸的母亲祈祷诵经。但他万万想不到,回到寺中没几天,1946年的正月初八,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,带着有枪来寺中拜年,一时不慎,手枪走火,伤及常修老和尚的大腿。老和尚年事已高,抢救无效,一星期后就与世长辞。在短短的一个月里,慈母与恩师都先后离去,永惺痛不欲生,“如可赎兮,人百其身”他心中真有宁可伤亡的是自己而不是两位对他恩深义重的老人家啊!至此他的精神已崩溃到近颠狂的地步。
殓葬了恩师之后,他自感不能留在增福寺的伤心地,于是他与新结识的又豁法师,去了附近的四官营“老爷庙”中暂住。
化悲心为道心
慈母、恩师的不幸,年青的永惺在悲痛之余,心中总有种忿忿不平的感觉,为什么两位都是护持佛法、慈爱为怀的长者,上天为何如此不公,为何好人不受到佛法的护荫。他一向平和、愉悦的心开始躁动了,一向坚定、恪守的信念开始动摇了。此时此刻,幸得亦师亦友的又豁法师,他见永惺精神状况如此不稳,一直的紧紧地跟随,耳提面命对他勉励有加,使永惺的心情得以逐步的平复下来。就在这段令人悲痛欲绝,举措失常的日子当中,说也奇怪,只要永惺稍有回俗的念头,就一定会梦到忘母的身影,她总是怒目而视。忘母一而再,在而三地入梦而来,虽未置一词,但慈颜竟便怒目,永惺深思,那是母亲对他道心动摇的不满啊!为何自己会如此躁动?对如来家业如此轻率?这哪里像一个受具足戒的僧人的仪范?为了告诫自己不能再犯,为了告慰忘母与恩师在天之灵,永惺在多位寺中的师友见证下,跪在三宝佛前,卷起衣袖,在右臂上燃灯以明心志。
灯蜡与油火在臂上灼烧,这位佛前弟子,不但有着刻骨的剧痛,也定下了刻骨的道心。
战场中的法会
回复平静的永惺,笃定本心,一生奉献佛法。他细致地观察了佛门以外的时局。这时候,国共两军为争地盘,各抢占阵地,各阵重兵,大家都在剑拔弩张,却又在互相忌惮,未敢贸然开火。就在着战火阑珊处,竟然是出现奇妙的平静局面。
经历过流亡和丧亲之痛的永惺,对民众的悲情,感同身受。他觑准了战火爆发前的平静,立即与寺中各师友及附近的相亲相议,举行一次安阴利阳的盂兰盆法会,他希望以梵呗佛号,稍慰众生的悲苦。
“这是一场僧俗同心,佛法无边的法会啊!”永惺法师回忆当年景况说。
这是当地首次举行的盂兰盆会。
“法会一连多天连消永昼的举行,寺中的僧侣领着前来参与的居士,诚心地祷颂。我们白天诵经拜忏,晚上放焰口。国共两方的士兵总在远远地监察着,既不过来问讯,也不敢捣乱,大概他们此刻都感到梵音的威力,受到感染吧!”
仪式一直顺利进行,直至到七月十五送圣完毕,都未受到干扰。一场战地上的盂兰盆法会,天人都得到法力的抚慰。
法会一过,这边四千多得国军、另一边数百共军,竟一涌而至,就在法会的场地附近厮战起来。
法会以后,永惺的声名,在附近一下子就传扬开了。有人跑来找他说,愿意将弃守的佛寺送给他。于是,他约同几位师兄弟一同前往察看。原来那是一所修建于荒田中的小寺,由于弃守多时,早已破旧不堪,但永惺不以为嫌,因为他只想有一安身立命、清修自处的小庙,于是欢天喜地的立即着手修葺。
大概是天公有意让这位年轻僧人多受考验吧!才找来铁锤、铲、凿等等工具,卷起衣袖动工,永惺双手拿起凿子在大石上立着,他让另一位师兄用锤子锤下,以碎散拦路的大石,岂知铁锤竟直直地往他手上砸下来,这可是重重的一击啊!永惺的右手食指,立时粉碎。他痛彻心扉,但只见他咬紧牙关,用左手把已变成一团的食指,捏着捏着,口里还安慰那挥锤的师兄说,没事的……
这右手的食指如今还在,由于肉里的骨头碎了,变得细细的很不像样。手指受伤以后,因为没有药去治疗,一直化脓了好几个月。修葺小庙的事只好延缓下来。回忆此事,永惺有感而发的说:“按佛门得苦行传统,很多僧人都燃脂明志,就把这一次的创痛,也视作一次自我考验吧”。
永惺在老爷庙再住了几个月,时局日趋紧张,战火已在弦上,战争一触即发了。东北已成战乱特区,故乡亦非安居之地。永惺只得汇同附近各寺院共十名出家发僧,结伴入关。
经过万水千山,长途跋涉,一路南来。穿越过众多东北乡亲闯关必经的山海关后,取道天津、溏沽,在而转乘轮船,经多天的驿旅以后,1947年2月终于来到浮华世界——纸醉金迷的大上海了!
抵上海,喜闻佛法
当年的上海,未受战火的侵凌,仍然是五光十色、灯红酒绿,看来一如太平盛世。然而这一切方内的浮华,对这位年仅二十一,风华正茂,但饱经乱难,并且在佛前许愿永不言退的僧人,却是水不扬波,心无罣碍。
这期间从东北、华北战区逃难而来的出家人,拥满了上海各个可供挂单的寺院。永惺与十位流离失所的云水僧很幸运地能暂时挂单在普济寺中。既然已落脚于此,初来埗到,安单之后,永惺就开始了解上海佛教界的状况,好确定自己的去向。毕竟,他是一个佛门的理想主义者,纵使在最艰难的时日,他都不愿意当一个粥饭僧,他要求自己度己度人,能以经忏生活,但更要深入经藏,对佛理融会贯通,才能真真正正地行走在菩提路上,担当起如来家业。
得知上海当地佛法兴隆,高僧云集,法筵常开,但外来的僧侣因言语不通,很难立足。他想既然如此,是否也好利用此机缘,多参礼大德高僧的经座。因此,他请普济寺的退居方丈,寿冶法师为他安排,让他与成观法师一起,去听当地大德的经课。
“寿冶法师就是后来在香港跑马地创办光明讲堂,然后再到美国住持光明寺的大和尚。”永惺特别为笔者介绍说。
回想这一段逃亡中的生活,永惺自问比当时任何一位落难的僧侣都幸福。寿冶老和尚不但安排他们每天上午到南市“沉香阁”听应慈法师讲《华严悬谈》、下午听南亭法师讲《楞严咒》,还每天给他们路费和饭费,使能安心地参礼听经。如是风雨无阻地听了八个月,那是永惺第一次参礼正式的大座经筵,他感到受益匪浅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这两位讲经的法师,都是佛教界中的佛学精英。就以应慈法师为例,他是后来中国佛教协会和上海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。因校繕重刊湮没了一千多年的巨著《华严疏钞》而盛名,他以“华严座主”自号,一生不作方丈,专注于研究和阐扬华严宗。
由于他讲述的经文都经自己繕校整理和研究,因此不但文义清晰,且其研究方法很有作用。
到了当年的农历十月中,经验虽未完,但由于普济寺的道济法师将到普陀山朝圣,他约永惺同行。因为机会难得,永惺自忖留在上海,立足的机会不大。一向以来,他都有访名山道场和参拜游访的心愿,现在逃难南来,也正好争取每一个机缘以增进自己的见识和智慧。
普陀山,观音菩萨的道场,是浙江的“海天佛国”。永惺在这里遍礼全山大小寺院胜绩以后,住在道济大慧寺的祖庭“西来院”任大殿的香灯。
永惺法名由来
几个月后永惺决定离去,到舟山定海,看望一年前与他结伴从东北南来,在他参痛失意时对他开解慰勉的又豁法师。他们一起到上海后,又豁独自去了舟山群岛,住在定海竹隐庵中参阅经藏。他们在庵中共住了几天,细诉别后的各自生活。良人别离时,又豁法师再一次对永惺殷殷寄语说。彼此都是落泊天涯的云水僧,今后命运如何不得而知。他觉得永惺年少出家,起始时虽未有很大的定信心念,但几年下来,虽云经历惨痛,这真正也是磨炼,尤幸总在佛门中遇良师的教化,加上起信后的宗教虔诚,由虔诚而精进所产生的证悟,一点一滴地抵消了凡俗之念。由于永惺过去曾有过迷惘的日子,因此又豁法师替他把原来“演霖”的法名,改为“永惺”。永字意恒定,惺字是醒悟、机灵。这象征着新生,希望他能在别井离乡后,忘却一切不幸与不快,重新起步,立志于接继佛陀的弘法使命。
这是永惺与这位挚友良师最后的一次见面了,自此天各一方,无缘再聚。
杭州灵隐寺的经忏生涯
别了又豁法师,永惺起程到杭州的灵隐寺去了。到灵隐寺的原因,参访是其一,但考虑到这名山大寺,或可挂单住下,因为总不能游脚四方而无定处。况且自己经受过观音寺佛学院的基础佛学教育,有听过应慈法师的经讲后,很想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。听说倓虚老和尚在青岛湛山寺办的佛学院很是不错,若能在灵隐寺挂单后,在筹点路费,那或可成事。
1947年中,中国大地上已战云密布,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火转剧,中共兵力,势如破竹,节节胜利,直闯关内而来。双方在关内与北京一带,也开始酝酿部署兵力,以求一站以定江山。因此,大家都知道华中的上海、杭州一带虽云未被波及,但看共产党自东北开站的势态而言,大军南下之举,就在眉睫。
灵隐寺,在太平盛世时当香烟缭绕、善信如云,但在如此时局,寺中僧众也度日如年,只靠粥水粗粮为生。永惺能在此挂单住下,说来还要感谢他的剃度恩师常修老和尚的教导。因他从老和尚处学得一身相当不错的经忏唱诵念打功夫,经灵隐寺住持考核过后,永惺进入禅堂当悦众。
“那些日子,我都靠赶经忏维持,钱很少很少。寺里的粥水稀薄,我那时正年青力壮,挣到的钱,一半都花在买素面吃去,否则,我连外出去做法事的力气都没有。”永惺不无感触地说。“但为了筹足到湛山寺的路费,我可是从不乱花钱!”
这位当时年仅弱冠僧人,在云水天涯、衣食不继之际,仍一心奋力于以“经藏”来解答自己“出家所谓何来”的疑问。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,如今想来,永惺有唏嘘之叹。他深有感触地说:
“我受东北观音寺的圆照、专修两位法师和上海的寿冶老和尚的关爱,给我一个很好的条件和环境,专心学佛。这是我为什么在七、八十年代,先后在香港兴办僧伽教育的原因。我在乱世中都能承此福荫,在太平盛世中更应承传。但情况则刚刚相反,反而是学僧难求,这是多么遗憾啊!
入读青岛湛山寺佛学院
漫天战火的中国大地,可供研习佛学的僧伽教育场所不多,青岛湛山寺所办的佛学院,已成了各地有志青年比丘向往之所。湛山寺是倓虚老法师在叶恭绰居士的护持及无数佛教徒的施助下,于1934年起兴建的,规模相当宏大,直到1947年才基本完成。在修寺期间,已陆续地兴办佛伽教育,他虽宗法天台,自己阐经演教外,更为学僧不惜礼聘他宗著名法师如慈舟、弘一法等到湛山寺来教学。
当永惺在灵隐寺储足到青岛的船票费用后,已是1947年7月下旬了,到了湛山寺佛学院,经过入学的甄别式,永惺被选录在“正科”修读。
湛山寺佛学院的学制分设预科、正科、专科、研究科四班,这体现了倓虚老法师对学僧的体贴爱护,他办学有三不限,与别不同,完全是应了当年中国僧人的普遍特质。其时僧人大多失学,他认为,年青的固需求学,但中、老年出家而又希望能学佛理就更应照顾,于是不限年龄、不限程度,不限来去。来者经甄别试后就按情况编班入读。
永惺在“正科”班中,除了修习佛学的基本经论外,也有国学的基本课程,连“书法”也有研习。
半年以后,倓虚法师偕同定西老法师自四面楚歌的战地传戒回来。定西老法师是当年永惺受戒时的得戒和尚。彼此经历过天涯云水,重逢于五年之后的青岛湛山寺,彼此都唏嘘不已!
永惺除了在课堂上恭听定西老法师开授的几门重要课程,如《法华文句记》、《八识规矩颂》、《十不二门指要钞》等等外,课余之暇,参加定老在寺内东院佛堂所成立的“念佛会”,在研习经论之同时,兼修净土。这也是永惺跟随定西老法师学佛的起始。
颠沛流离,继续难逃
无情的战火终于降临了。北京已陷入战围之中,难民不断南下,不少涌到青岛的市区来。原先这个风景秀丽,有东方瑞士之称的城市,顿时风声鹤唳。爱护学僧如子的倓虚老和尚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与安排,决定由定西法师和乐果法师,率领五十多位学僧,在九月二十日前后,由青岛避难到上海去,暂时挂单在天台名宿兴慈老法师主持的法藏寺中。
事实上,大家都清楚法藏寺只能作为暂且栖身的中途站,这里是无法容纳一大批僧众的。因此,各人都各自想办法解决困局,也就是说自找出路。在喘息未定之际,定西老法师,移单到浦东的海慧寺去了。
永惺此时顿失所依,加上北方战局已逐步南移,心情极为难受。细想留在华中一带,迟早也是会再陷入乱局之中,加上从同道中听到当代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,正在广东曲江南华寺,讲经说法,于是心中又生起南下到广东去,好远离兵燹,听经闻法的念头。
这时候,像永惺那样考虑远离战火,避祸南下的人何止数亿万计。南下的路上,他又重蹈三年前自观音寺逃难回乡所遇的境况,再次令他感到沮丧和难受。
永惺与同学畏三法师一起,自上海乘浙赣线火车,经杭州到湖南株州,再南下到达曲江南华寺。沿途所见,难民拥挤杂沓,哀鸿遍野。永惺坐在火车顶上,车头烟囱上吐出的煤屑,尽往脸上头上飞扑而来。由车顶下望,铁路两侧,尽是无法赶上火车的难民,一张张绝望、惊惶的脸孔。四周是妻离子散的哭唤、伤残病患的哀嚎,路轨两旁层层互叠的死尸,底层的白骨依稀可见。那些都是多天以来逃难南下时从火车顶上掉下的同胞。永惺闭目哀叹,感到有如置身地狱,口中不断诵念佛号,祈求这些孤魂能得以往生极乐。
天涯云水,历尽苦楚,坎坷的战乱经历,是永惺感悟和引证佛道的最好机缘,生命的无常与有限,都充份展现在哀鸿遍野的时局中。
经历了七天有如身坠阿鼻般的苦难旅程,永惺和几位同学终于到达曲江南华寺。这里的方丈是复仁老和尚,首座是本焕老和尚。而南华寺中佛学院的主讲明悟法师,恰巧又是永惺在长春般若寺受戒的引礼师,因此安单下来心神稍定。
在南华寺等了一个月,还未有虚云老和尚会到南华寺来的消息。打听之下,虚老在乳源的云门大觉寺正忙于修寺的工程之中。既然老和尚不来,永惺便聊同几位湛山寺的同学,结伴到一百二十里以外的乳源大觉寺去参访。
几位学僧几经艰辛,顶着风雨走了百多里的路,拜会了一百一十岁的虚云老和尚。永惺还记得抵达当夜,已是晚上九时多了,甫入寺门,仍见一老和尚穿着破草鞋,挑着汽灯,在泥洼满布的工地上,监督着修寺的工程。多感人的情景啊!老和尚虽未开示但这种辛勤操持如来家业的态度,已成了日后永惺每事恭亲,孜孜不倦,从不言休的身教体现。(拜会详情见序章《留点福德后人修》)
在云门寺住了三天,永惺拜别虚老经韶关乘火车到广州在六榕寺挂单住下。
六榕寺的住持明观老和尚,受虚云老和尚之委托出任六榕寺住持,得知几位来自山海关外的僧少年,历尽了千山万水,刚从乳源拜会过虚老而来,立即接待他们住下。明观老和尚就是日后香港荃湾三叠潭东觉禅林的开山祖师。他1949年以后到港,从此弘法香江。
此时已是1948年1月,农历新年将至,几位学僧在远离家乡、远离战火的南国一隅,稍定心神,还来不及思索今后的去向,尚感前路茫茫。新年刚过,就接到先期已到香港的湛山同学——乐渡法师来信,说倓虚老法师已抵港,并准备筹办“华南学佛院”以继续青岛湛山寺佛学院的未完使命。佛学院预留一学位给永惺入读。得此喜讯,有如得到脱离苦海的通行证一样,永惺欣喜不已,立即整理行装,匆匆奔赴香港而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