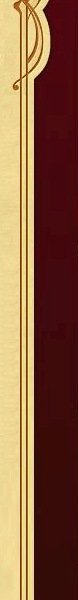关键词:批判佛教、大乘三系说、中国佛教史三期说、哲学的非整体性尺度、史学的整体性尺度
20世纪的中国佛教,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反省中渡过的。高僧大德、佛教学者,始于对宋元以降佛学传统的检讨反省,继而对中国佛教屡屡发出严厉的批评,借印度佛教的正统来贬抑中国佛教的传统。譬如,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说:“自天台、贤首等宗兴盛而后,佛法之光愈晦。”[1]日本学者甚至提出“批判佛教”一词,加强了对中国佛教传统的批评力度。
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,我们也要对这股批判之风作出某种反省:一、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,有没有改变佛教的根本大义?二、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,有没有特定的历史语境?通过对“大乘佛教三系说”和“中国佛教史三期说”的诠释分析,本文提出“哲学的非整体性尺度”和“史学的整体性尺度”,试图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佛教。
一、“批判佛教”的焦点
从南北朝末年开始,约在6—8世纪二百年间,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宗派。一般认为,中国佛教有八个宗派,即天台宗、华严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唯识宗、禅宗、净土宗、律宗和密宗。这些宗派的出现,使佛教从一种外来宗教变为民族宗教,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,乃至于现代的许多中国人不知道佛教原来属于外国文化。从宗教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,这种情况无疑是成功的。但在20世纪的批判佛教看来,中国佛教的成功,正好暗示了印度佛学在中国的失落。这种局面,被台湾佛教学者蓝吉富称为“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”。[2]
欧阳竟无(1871-1943年)和太虚(1889-1947年),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堪称“双峰并峙、二水分流”,分别领导了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,培育了大批佛学研究的专门人材。有感于中国佛教当时的种种积弊,他们致力于佛法的改革与振兴,寻求一种能够适应时代、契合众生机缘的新佛教。欧阳竟无认为,佛法的复兴,必须要通过唐宋以后逐渐失传的法相唯识学,回归印度佛学的正统;太虚认为,佛法衰微的原因,是长期以来重消灾超度的鬼神化倾向,因此他要建立不重鬼神而重人乘的 “人生佛教”。[3]
支那内学院包括吕、王恩洋等人在内,他们认为,真常唯心系的经论如《大乘起信论》,都属于“伪说”,印度的大乘佛教只有“中观”和“瑜伽”两个系统,其中只有瑜伽大乘即唯识法相学才能体现佛法的中道,属于“非有非空”的第三时圆满究竟法。欧阳竟无在《唯识抉择谈》里,列举五蔽来批判中国的传统佛教;吕进一步指出,天台宗等中国佛教,实质上奠基于对印度佛教的误读,强调中国佛学的根基在中国[4],把“心性本净”、“心性本觉”作为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分野,指斥中国的传统佛教不符合印度佛法的原意。
和支那内学院这种激进态度相映成趣的是,武昌佛学院太虚、印顺等人的温和态度。太虚主张回溯原典,托古改制,对传统的八个佛教宗派作出新的判释,把它们归纳为大乘佛教的“三系”或“三宗”,即“空慧宗、唯识宗、真如宗”,提倡中国佛教的八宗平等,主张大乘佛教的三宗共扬。他说:“唯识等大乘八宗,则均以实相法界——即诸法唯心为根本,及妙觉佛果——即无上菩提为究竟。以此根本义故,究竟义故,同一大乘平等。而就其集理起行之特点,以明其教理所趋重所崇尚之宗主,则昔于佛法总抉择谈中,尝大别为三宗。”[5]太虚用“空慧宗”诠释三论宗,“唯识宗”诠释唯识宗、律宗,“真如宗”诠释禅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净土宗等,认为天台、华严、禅等诸宗都是佛陀的圆觉教法,而法性空慧和法相唯识只是圆觉大乘佛法的分流。欧阳竟无提出要由唯识学转变到唯智学,但在太虚法师看来,所谓“唯智”即是他所说的“真如宗”。[6]印顺法师的思想是接着太虚发展而来的,他提出了“性空唯名”、“虚妄唯识”和“真常唯心”三系说,不同的是,印顺认为在大乘三系里,唯有“性空唯名”一系真正把握了佛教的精神,其他二系特别是真常唯心系,已经不是佛教原意,夹杂了梵我外道思想。因此,像天台、华严等这些受到唯心思想影响的传统宗派,算不上是究竟之法,他主张回归坚持般若中观学的三论宗。也就是说,代表中国传统佛教主流的太虚一系,最终也对最具中国特色的几个宗派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。
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反省态度,在日本学界也有明显的表露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两位日本佛教学者,驹泽大学松本史朗和衤夸谷宪昭,引发了所谓“批判佛教”的争论。这场讨论反响热烈,1993年“美国宗教学会”年会专门为此安排了专组讨论。这两位日本学者认为,“本觉”、“如来藏”思想不属于真正的佛教,甚至把汉传佛教思想称为“伪佛教”。这种“伪佛教 ”,在社会实践上维护现状,保守反动,与他们所认为的“真佛教”背道而驰。受西方批判哲学的思想影响,他们认为,佛教本应是一种批判哲学,真正的佛教应该是有社会关怀的“批判佛教”。[7]我们在这里应当指出,日本学者所谓“批判佛教”的“批判”,与本文所说的“批判”含义不尽相同,前者指佛教应该有社会批判的功能,而不是一味地投合妥协,后者指对传统佛教的反省与检讨。但是,“批判佛教”是在对传统佛教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的,这种提法加强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佛教的反省意识的认识,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用“批判佛教”一词涵括20世纪中国佛教重反省求改革的特征。
无论是在中国,还是在日本,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辨别佛教的真伪,重新认识中国佛教的正统地位,特别是检讨真常唯心思想的正当性。从南北朝末年开始,中国的佛教宗派,一方面通过判教,把自己的教义界定为最圆满的佛法,一方面通过编造传法谱系,论证自己在历史传承上的正统地位。但是,到了近现代,学术昌明,考古学、文献学、语言学有了长足的进步,许多学者根据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,否定了这些传法谱系的真实性,对于大乘佛教经典的成立史提出了有力的质疑,认为这些宗派所依的汉译经典有些属于误读误译,有些甚至是中国人的伪作,特别是那些宣扬真常唯心思想的经论,譬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、十卷本《楞伽经》等。
真常唯心一系的经典,因此成为众矢之的。这类经典,在中国佛教史上确实占据了核心的思想地位。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法师,既然设定了以印度佛教为正统的标准,特别注重梵文印度佛教文献,传统的中国佛教的正当性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。他们把印度佛教文献里有的思想视为正统,没有的视为旁出,特别地关注、批判佛教在中国社会受本土文化影响的地方。本文认为,他们的这种态度有失偏颇,并不足以论证真常唯心思想是大乘佛教的歧出,而且,这种态度显然抛离了中国佛教的历史语境。
二、反批判的理论
我们现在试图从两个层面作出“反批判”,检讨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思潮。第一是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层面,说明中国佛教并没有偏离佛教的根本,我们这里借用 “大乘佛教的三系说”,说明中国佛教里的“真心”思想未必虚妄;第二是宗教史或社会史的层面,说明宗教传播并不单纯是宣传学术思想,我们提出中国佛教史的三期说,诠释中国出现佛教宗派有其不得已的历史情境。其实,像天台宗这样的中国佛教,既要“契理”,又要“契机”,之所以能在中国社会立足,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何等艰难的努力!
1、大乘佛教的三系说
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,太虚曾经提出“三唯论”,把大乘佛教分为“唯性”、“唯识”、“唯智”,后来又提出“三宗论”,“唯性”指“空慧宗”,“唯识 ”含义不变,“唯智”指“真如宗”。印顺法师的“大乘三系说”,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。尽管他批评了真常唯心思想,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“大乘三系说”反驳 “批判佛教”,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回复到太虚法师三宗共扬的态度。其实,真常唯心思想未必就是印度佛教的旁出,牟宗三从义理上论证了这种思想的合理性。
支那内学院屡屡贬斥“如来藏”、“真常心”一系的经典,认为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藏,一识二名,《楞伽经》里的“如来藏藏识”就是指“藏识”。[8]吕在《起信论来历的探讨》里提出,《起信论》系重蹈魏译《楞伽》误解而自成其说,认为首先要解决“如来藏”与“藏识”的同异问题;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:“藏识即阿赖耶,即如来藏,《楞伽》、《密严》均视如来藏与阿赖耶为一也。”[9]印顺虽然指出“真常唯心”在印度佛教里源远流长[10],但也认为这种思想有与梵我外道相混的危险。牟宗三在他的《佛性与般若》里,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,认为“如来藏藏识”包含“如来藏”和“藏识”两层意思,是清净识和染污识的和合。他认为,这样的思想,虽未必就是印度文献里原来就有的,但也不至于违背了佛教的根本意思,像《楞伽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起信论》等,与玄奘所传的虚妄唯识学只是两个系统而已。[11]他甚至认为,支那内学院所说的虚妄唯识系经典,在理论上还不及如来藏系经典圆满,因为要是以虚妄染污的阿赖耶识作为万法生起还灭的依据,完全依靠“正闻熏习”实现转识成智,达到清净无漏的佛境,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无限过程,从理论上说很难最终保证众生一定会有成佛的可能性;要是以自性清净心作为起灭的依据,众生成佛就有了理论上的保障。
既然真常唯心的经典可以自成一系,甚至比起虚妄唯识思想更为合理,牟宗三因此在《佛性与般若》序里说,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,其实还是一个佛教,并没有两个不同的佛教,中国僧人把佛教里带进来的印度的社会历史背景搬走了,但佛教本身并没有变质,直称经论的义理而发展,这些僧人也没有和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完全契通。[12]中国佛教原本没有偏离佛教的根本大义,都还接着佛陀的一代说教继续发展,所谓“三系说”,指的还是一音说法,就好像《华严经》所说的“ 心、佛、众生”三法无差,也好像智岂页所说的“三谛圆融”。
佛教传入中国,必然要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,去适应中国社会,否则难以生存。我们立论的根据,也就只能看他们的宗旨有没有偏离佛教的根本大义,对于纯粹文献上的“正统”、“原意”,应当有比较宽容的理解。佛教的根本大义,一旦表述为语言,进而表述成文字,这看似是思想的展开过程,其实也是思想不断被凝练的过程。后者意味着,所谓“原意”、“正统”,在语言的运作中已被不同程度地封闭、隐埋于特定时期的文化背景里。因此,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,思想已经很难有被完全理解的客观性。原始理论如果不是被简单地重复,势必会在不同的阐释中融入新知,理论的发展方向必然受到后续阐释者的调整和补充。但是,合理的阐释并不意味着“歪曲”或“误读”。
阐释的合理性,奠基于对某个理论问题的特殊嗜好。如果我们脱离了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,实际上很难奢谈什么“原意”或“正统”。我们现在怎么可能了解佛陀生前的思想全貌呢?他的思想现在早已被分成了许多部分,不同的宗派各在发挥其中的某些问题。我们对这些宗派的评价,只能看他们在这些特殊的问题上有没有坚持佛教的根本大义。这种态度,我们不妨称之为“哲学的非整体性尺度“。
举例来说,我们如果把天台智岂页的思想分成“三谛圆融”、“圆顿止观”和“一念三千”三部分,分别代表佛教的“境”、“行”、“果”,那就要看他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违反佛教的根本大义。天台宗的这套教观体系,在这些问题上坚持了佛教的根本大义,即使与某些经论的原意不甚相符,也不应说是违背佛法。智岂页思想在天台宗内部是有原创性的,但和整部佛教史相比,这套理论也只是一种合理的阐释,智岂页在现实社会里有他不得已的历史情境,因此也有他特殊的理论侧重点。即使拿中唐湛然、北宋知礼的天台学来作比较,我们也会发现,他们的天台思想与智岂页也不完全相同,因为这些天台后学也有他们自己所面临的时代任务,有他们自己的重点。我们既然很难完全还原所谓的“原意”,何必又要执著呢?关键是要分析理论产生和传播的机缘,剖析他们的理论生长点。
2、中国佛教史的三期说
“三系说”奠定了我们理解中国传统佛教的原则,现在是要具体分析像天台宗这样的传统宗派之所以出现的理论机缘,也就是具体的历史情境,我们为此提出了中国佛教史的三期说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按照佛教与中国社会互动的实际过程,从佛教不断地世俗化、现实化的角度,我们把中国佛教史分为三个时期,学理佛教、民俗佛教和人间佛教。
第一,从两汉之际传入到晚唐,称之为“学理佛教”时期。我们把它细分为三个阶段,一是从两汉之际到东晋末年的四百年,所谓“格义佛教”,二是从东晋末年到南北朝末年二百年不到的时间,所谓“学派佛教”,三是指隋唐三百余年,所谓“宗派佛教”。这三个阶段统称为“中国早期佛教”,这一时期以佛典输入、学理会通为主;
第二,从五代、北宋到晚清,称之为“民俗佛教”时期。这一时期以佛教与民间社会的民俗生活日益融合为其主要特征;
第三,自晚清的佛教复兴运动迄今,称之为“人间佛教”时期。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现象是,以开放的心态去包融西方的哲学、宗教思想,提倡佛教的现实化,主张佛教为现实的人生服务,祛除传统佛教中巫魅迷信的成分,塑造佛教在现代社会中净化人生的新形象。[13]
这种对中国佛教史的三期划分,重点是在分析中国社会与佛教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。我们以前的研究主要是讲学理,谈论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,所以在理解佛教史时,往往是以个体僧人、义学发展为叙事主线,进而把宋元以后的佛教视为一片衰败景象。我们现在用“三期说”重新审视佛教史,以僧团力量在中国社会的消长为叙事主线,可能会给中国佛教史的学术研究开出新境界,对于历史上的那些佛教宗派会有一些新的同情的了解。这就意味着研究方法的转换。
就早期佛教史写作而言,通常是以个体僧人、义学发展为叙事主线,这以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为典范;此外,海外汉学家里还有一些从社会史角度研究,最有名的是许理和《佛教征服中国》,这位作者认为,佛教传入中国“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,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——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”[14],也就是说从僧团着手研究佛教的传播。以僧团为中心的研究方法,关注僧人的社会地位、寺院的社会功能,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反应。这里所说的“ 僧团”指以亲教师或寺院为纽带的僧人团体,一般不指称全国或州郡等地区的僧尼全体。
第一种方法有助于梳理佛典传译、义学思想演进等佛教内部问题,再进一步就可以写成义学发展史或范畴发展史,如牟宗三的《佛性与般若》;第二种方法有助于揭示佛教与世俗社会的互动关系,更容易摸清佛教的传播史。我们发现,在义学发展史背后,往往保留了一个世俗社会的参照系。譬如,历次政教冲突尤其是北朝的两次法难、疑伪经的涌现、造像运动、宗派的形成、佛教徒的末法意识,都有特定的社会史根源。我们不仅想找到佛教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既成事实,同时,还想找到中国社会对佛教的反作用力。僧团的出现,有时候并不是出于追随者的虔诚,而是为某种世俗力量造就的,这里所说的世俗力量并不指个体化的经历,而是指社会性的共识,譬如民众的祈福心态、政府的监督制度。
转换研究方法,寻找社会与佛教的相互作用力,可以帮助我们演绎学理佛教让位民俗佛教的社会史依据,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从学派佛教到宗派佛教的过渡。这种转换,在某种程度上,就是要求我们能对历史作出整体性的全盘考察。这种态度,我们不妨称之为“史学的整体性尺度”。在这个尺度底下,我们或许可以明白:一个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改变,这种改变不是出于对原意的歪曲,而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髓。作为后来的学者,我们其实无需一味地否定经过改革的宗教,只是希望这些传统的宗派能够重新表现出某种思想的活力,为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。20世纪的佛教学者,有一股反省中国佛教的潮流,包括日本的“批判佛教”在内,借印度佛教的文本否定中国佛教,我们要从社会史的角度,对他们的反省作出自己的清醒判断。
关注宗教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避免宗教生活中巫术化的迷信倾向。但是,这种史学精神,并不局限于宗教传播、学说传承的客观真实性,还必须顾及宗教生活与社会文化整体的互动关系,否则有可能陷到史料堆里,眼光狭隘,立论偏颇,无限地夸大历史的偶然性。譬如,智岂页反复讲“世间法不违实相法”,经常引证周、孔的儒家经典,体现了中国佛教试图贴近中国社会的良苦用心。我们知道,两次法难之后,中国僧人普遍有一种末法意识。时势逼迫中国佛教必须进行独立思考,如果死守印度佛法的文献传统,今日之中国恐怕佛教早已绝迹。
结语
为了纠正20世纪中国佛教的偏颇之处,我们提出“哲学的非整体性尺度”和“史学的整体性尺度”,用来客观地评价像天台宗这样的中国佛教,要求我们从义理的根本处着手,分析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;同时从特定的中国历史社会背景出发,同情地理解中国社会接受佛教的形式,仔细地辨别佛教宗派兴起的历史语境。佛教里经常讨论“不变”和“随缘”的问题,我们现在重新研究中国佛教史,既要分析中国社会这个“缘”,也要看到佛法大义这个“不变”,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。
注释:
[1]欧阳渐《唯识抉择谈》,张曼涛主编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第28册,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,第10页。
[2]参见蓝吉富《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》,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90年第2期,第52-55页。
[3]参见周志煌《唯识与如来藏》,台湾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,第1-8页。
[4]参见吕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·序论》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4页。
[5]太虚《佛法之分宗判教》,黄夏年主编《太虚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,第22页。
[6]参见太虚《佛法大系》、《佛法之分宗判教》、《再论大乘三宗》等文。
[7]参见林镇国《佛教哲学可以是一种批判哲学吗?——现代东亚“批判佛教”思潮的思想史省察》,释恒清主编《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发展——印顺导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》,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。
[8]参见欧阳竟无《楞伽疏决序论》、吕《楞伽如来藏章讲义》、《起信与楞伽》、《大乘起信论考证》等文。
[9]吕澂《楞伽如来藏章讲义》,《吕佛学论著选集》第1册,齐鲁书社1991年版,第258页。
[10]参见郭朋《印顺佛学思想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,第109-110页。
[11]参见牟宗三《佛性与般若》,台湾学生书局,1993年修订版,第325-326页。
[12]参见牟宗三《佛性与般若》,第4-5页。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,牟宗三认为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,实际上是基于儒家本位的立场而说的。在牟宗三看来,中国哲学的存有是体证的存有,所以是“无执的存有论”,并把佛老视为“非创生系统的存有论”,把儒家视为“创生系统的存有论”。他认为,佛老虽就实践体证面来开显无限智心,然皆未能就人的德性主体承当,儒家则能直接就人的德性主体来开显存有,这个德性主体既超越又内在。
[13]参见李四龙《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版)1996年第4期。
[14]许理和著,李四龙、裴勇等译《佛教征服中国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,第2页。
[ 李四龙 哲学博士,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]
(来源:国学论坛,引自中评网)